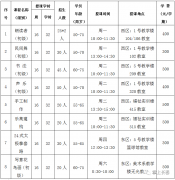|
当时自己刚刚签下一本美国历史学家彼得·盖伊研究西方中产阶级的着作《施尼兹勒的世纪》的版权,此书此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,译者为梁永安。于是莽撞人如我,便利用互联网之便,迅速搜到了梁老师,发现他任教于复旦,于是拖亲靠友,拿到梁老师的联系方式,稍作准备即打了过去。不想误认姻缘,电话那头的梁老师很抱歉地和我说,此梁永安非彼梁永安。彼译者远在海峡对岸的台湾,实在是一场误会。 然而,误打误撞,梁老师却和我在电话里聊起来西方中产阶级文化,特别是西方经典小说的话题。于是相约见面,见面后更是相谈甚欢,这样也就有了《文学七日谈》的出版设想。 梁永安是中文系的老师,讲了一辈子文学和电影,对西方经典如数家珍。又由于常年与青年人面对面,对年轻人的想法也很能把得准脉。加之近年来他在互联网平台,特别是在bilibili这样的 二次元“后浪”青年集散地网站上颇受欢迎。凡此种种,让《文学七日谈》这本与年轻读者对话的小书显得恰如其分。我阅读后,更是打消了担心此类“老少配”书籍中前辈对后辈居高临下的“爹味”。 之所以说没有“爹味”,首先由于这本书“无限交谈”的对话形式。通过大学教授和一位青年编辑,或者说一位伍尔夫意义上的普通读者(common reader)进行有关小说的对话。这种形式,让我想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“无限的交谈”。亚里士多德认为无限交谈不是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,而是一种类似放风筝的感觉——两个人拽着一个线头,撒了欢儿地跑,直到把风筝放飞,然后你拉拉线,我再拉拉线,让话题飘着却不断线。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,感受到的恰恰就是这种“收-放-再收-再放”的节奏。 而从编辑的角度看,这种方式要编排得一气呵成,就不能给人一段一段的割裂感,收与放毕竟是在一根绳子上,最好有连续的阅读体验,否则就会像读采访稿或者新闻访谈,一问一答,比较生硬。因此,在设计内文时,我抛弃了“梁说”“刘说”的方式,而是采用两种字体,老先生用端庄的宋体,青年人用稍显轻盈的楷体,这样既区分了对话的两方,又尽量保持住阅读的整体感。 和梁永安老师熟悉后,渐渐发觉他是“考试型”选手。什么是“考试型”呢?上学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——平时看起来平平常常,一到考试却能一鸣惊人。梁老师的“考试型”就体现在和你的交流上,看起来说的都是平常语言,但一旦讲到关键处,他往往语出金句,让人印象深刻。他的这些金句,全不说教而尽皆有趣。我想这也是这本对话书没什么“爹味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为此编辑这本书的时候,我与梁老师商量,在每一章里选择一些金句,仿照时下流行的“语录体日签”插入书中,一来作为阅读时的短暂休整(喘口气),一来也能增强这本书的设计感,让它显得更为有趣,便于青年读者在读书之余晒书、打卡。从出版后读者的实际反馈看,这个设计是成功的。 最后想说说这本书的内容,我觉得有点像“撬螺丝”,每一章聊一本书,看似是在解读经典,其实是通过经典看历史、看文化。书中的两个对话人,就像是卡夫卡《城堡》里的土地测量员K,通过谈七部西方经典小说,给读者拼贴一幅文化地图。两个人按图索骥,抽丝剥茧,为当下的读者探明那些曾在小说中发人深省,却早已遭人遗忘的历史坐标点,窥一斑便见全豹!撬动我们看似熟极而流的固有概念(工作、恋爱、自我、婚姻,等等),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困扰我们的选择、那些使我们焦虑的脱发、“压力山大”与“累觉不爱”,通通在小说的世界中入定,在深一度的阅读里,找到精神的树洞。 也因为内容的鲜活有趣,我在最初构想这本书的开本和装帧时,就抛弃了143mm*210mm的常规开本尺寸,希望可以做成一本能够在大家通勤时看的口袋书。走路时插在裤兜里,上车了抽出来读几页。不必因为是聊经典,就非得正襟危坐。恰恰相反,也许才能真的让经典进入寻常百姓家。而这也是梁永安老师出版这本书的最大目的和希望。 《文学七日谈》这本小书最大的优点是提出了很多大问题,且这些大问题都和现实生活中的你我息息相关。书中的两个人通过阅读小说尝试着去解答这些问题,其实面对这些话题,以对话的形式去谈,有点“举重若轻”, 解答的空间窄了点,深入思考的纵深还不够,对资深玩家而言肯定不够劲,不满足。 但一本没有“爹味”的经典解读之书,本身面对的就是有兴趣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普通读者,从这个角度看,谈话未始不是一种姿态,一种轻松自在的姿态,选择这种姿态,目的当然就不在于深入(那毕竟是更多象牙塔中人的饭碗),而是在这个到处要求“赋能”的时代,换一种看到世界的方式,聊聊没什么“钱途”的趣事。 |
热门关键词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