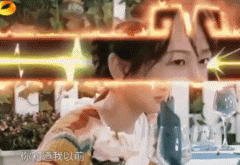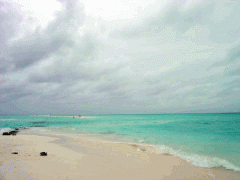|
《呼啸山庄》的译者(也是书名的中文首译者)杨苡于 1 月 27 日逝世。她与“五四”运动同岁,1919 年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大家庭。在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一书中,她如此回看这一时间上的巧合,认为自己“生逢其时”:“对政治、理论什么的,我不感兴趣,也从来没弄懂过,同时我与各种运动都是疏远的,但我最基本的判断和态度,或者你说常识、价值观也行,都是新文化给我的。这里面也包括对旧式家庭的态度。” 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是杨苡的口述自传,由余斌整理撰写而成,前不久刚刚面世,我们幸而能在她离世后,继续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位百岁老人坎坷的人生,以及她身处的时代。下面摘选的段落,讲述了杨苡在战乱时离开天津、准备前往西南联大途中的见闻,一位少女对逃离父权家庭的渴望、对家国破碎人何以自处的思考跃然纸上,而精神上更为自由开阔的人生正等着她。 我是七月七日下午上的船,晚上开到塘沽就停下,夜里没动,第二天早上才开出港口。母亲,还有七婶一大帮人到天津的码头送行。英国太古公司的“云南号”。很大的船,我母亲她们登上船,也是头一次,挺新鲜的,东看看西看看,到开船的时间,一晃也就过去了。她也没哭。倒是在家帮我理东西的时候,她流过泪。还问我,你就舍得离开家?舍得你这些宝贝? 我喜欢搜集各种玩意儿,唱片、明星相片……光是手绢,就有好几盒,有六条一盒的,十二条一盒的,都放在一只大箱子里。但我一点离愁别绪也没有。一直想离开这个家,像巴金笔下的觉慧那样,这回真的要离开了,要有自由了呀!在码头上我也还是一团兴奋。船离开码头时,船上的人都在跟岸上的人招手,船上也有日本人,他们的亲友就往船上扔彩带,还叽里呱啦大声说日语,大声叫:“沙哟娜拉!”讨厌极了。后来在船上遇到日本人,他们净是鞠躬那一套,我们能不理就不理。 我并不是一个人出远门,从天津到昆明,是跟中国银行的人一起走,都是中国银行安排的。一路上都是分等级的,行长、副行长、老行长(就是我父亲)的家眷待遇是最好的,比如我坐船都是二等舱,到海防住酒店住套间,大部分中国银行的人没这待遇。连我七叔家的纮武也只住三等舱。七叔那时是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,杨纮武是他的小儿子,我叫他“阿毛弟”。同船去的中国银行的家属中,只有他和我最后到了昆明。我们都进了联大,关系特别好。 过去的客轮,二等舱是最好的,两个人一个房间(还有一种叫“大餐间”的,也是两人一间),二等舱上面并没有一等舱,单人房间要特殊的人物特殊安排才会有。三等舱、四等舱是什么样,我不知道,二等舱和下面是隔开的,应该是可以下去的,我是第一次出远门(之前只是坐火车去过几回北平),也没敢乱走。好像四等舱就不太行了,睡四等舱的大都是流亡学生了——其实里面不少在家里也是少爷,家境糟糕的这一趟也走不起。 虽然是隔开的,下面的可以到上面的餐厅来吃饭,杨纮武就到上面来吃,是打了招呼的。当然也要吃得起,我们都是中国银行安排好的,究竟在餐厅里吃是什么价,我也弄不清。想来是挺贵的,因为都是吃西餐。那时不管在哪里,吃西餐都比较贵。吃饭时二等舱的乘客服务员会到房间来请,叫服务员都喊 boy,他们都是说英语——英国人的船嘛。到了晚上,大餐间里有舞会,男男女女衣冠楚楚的。我没去过,觉得跳舞的和我不是一类人。 我喜欢在甲板上看风景,没坐船出过海,什么都新鲜。还有就是唱歌,唱那个“一心去航海,海风使我心忧,波浪使我愁……”。和杨纮武一起住三等舱的有个李抱忱,北平艺专教音乐的,因为纮武的关系就认识了,我们天天在一起唱歌,一首接一首地唱。其实一点也不愁,唱就很开心,但一出塘沽口我就开始晕船,那就不好玩了。我开始吐,什么都不想吃,李抱忱说,不吃怎么行?硬逼着我喝点番茄汁什么的。 航行了好几天,到上海要停一天,我就在上海玩了一天,住在颜惠庆家。颜惠庆这个名字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,他清末的时候就搞外交,公使、外交部次长、外交总长都当过,在北洋政府还组过阁,当过总理,老资格了。那些官衔什么的,我其实闹不清楚,只记得小学时有次看电影,新闻片,上面有他的画面,是个外交场合,他不肯签不平等条约,卷了国旗回国了。我们太小,事情的背景不清楚,只是觉得同学的爸爸出现在电影里,特别好玩,一起朝颜枬生看,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。 前面说过的,我和颜的女儿颜枬生一起在中西读书十年,好得不得了,是真正的闺密,我姐和她姐也是同学。因为同学关系,两家大人也有来往。母亲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,总是被歧视,和高门大户人家的太太不怎么打交道的,和颜家是例外,颜伯父、颜伯母(我都是这么称呼)都是特别开明的人,一点不摆架子,所以母亲特别愿意我和枬生交朋友。其实母亲和颜家大人也没怎么见过面,毕竟她是姨太太,怎么称呼都是问题。间接的打交道只有一次,是我在她家吃饭,她家养的狗老在桌子下面蹭来蹭去,我拨拉它它也不走,结果不知怎的把我衣服上弄了个口子。吃完饭颜伯母瞧见了,问明情况,第二天就买了块料子让下人送到我母亲那儿,表示很不过意。这事母亲一直记着,对颜家的印象特别好。我也喜欢和枬生一起玩,到她家玩也开心,因在她家一点不拘束。有次玩捉迷藏,我跑到书房里,颜伯父正好在那儿,我不知往哪躲,他就示意我钻到桌子下面去,还帮着打掩护。 卢沟桥事变后,颜枬生全家就搬到了上海。在上海,颜家老大(我们都喊他“颜大哥”)接了我就到家里。枬生正准备到美国留学,颜伯母一见到我就说,别走了(意思是别去云南了),和枬生一块儿去美国念书吧,我来供你,你母亲肯定愿意的。我知道母亲多半赞同(跟颜家的人在一起她是最放心的),我也不反对留学,但是我和大李先生说好了的,要在昆明等他,一心就想这个,就根本不考虑其他了。 在上海,颜大哥开着车带我去逛。他家有三辆车,载我的那辆是敞篷的,开到一个刚修好的漂亮的游泳场,很摩登,好些电影明星到这里来游泳,我们不下去游,买了饮料冰激凌坐在旁边看,不游泳吃冷饮看着的人还不少,就像我在天津去国民大饭店的舞场,也不跳,就看热闹。这样的游泳场,不光是健身,也是高档消费的地方。上海号称“十里洋场”“东方巴黎”,比天津还要时髦得多,颜大哥带我到处逛,也是让我开开眼的意思。我当时一边瞧新鲜,一边心里就想,日本人都打进来了,还这样,这不叫“醉生梦死”吗? 一天以后,又上船往香港走,香港是这条航线的终点,从香港再往越南的海防,就要换法国轮船公司的船了。等那船船期,我在香港又停留了十天。 在香港,我住在卞白眉家,好像是在浅水湾那一带,山坡上挺大的一幢别墅,叫“湾景楼”。卞是我父亲指定的中国银行行长,接替他的位置。卞是扬州人,留美的,说英语有方言味,除了这一点,其他方面,洋派得厉害。—说起来也是沾亲带故的,我有个堂姐,七叔家的,叫杨漪如,就是卞家二少奶奶。 这次中国银行的许多人一起到香港,说是旅行,其实是从日占区撤出来,在香港已经成立的津港办事处,就是在预做准备。我们因为要到大后方读书,跟着一起走,好有人照应。到香港后,当时是天津副行长的束云章就对中国银行的子弟说,大后方的生活很艰苦,劝我们不一定要去,果然,大部分人就留下不走了。又有一次,卞白眉请坚持往大后方去的几个人吃饭,吃饭之前讲话,说了些读书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读书一类的话,还说我们可以到大后方去,要留在香港也可以。其他就记不得了,只记得我们肚子饿了,巴望他快快结束,他还是讲个没完。我根本没考虑留下,脑子里就想着和大李先生的约定——“昆明见!” 住在卞家没事干,我就一个人坐电车到处转悠。不会说广东话,没法问路,也没关系,反正会坐车就行。除了自己玩,我还和李抱忱约好了一起逛过大街。他是老师辈的,又和大李先生熟,他说过我一次—我们约了在车站见,一见到他,车还没停稳我就跳下来了,他就说我,还没到站车不会停的,跳下来弄不好就跌着。我说,李先生我看到你了呀。 我们在一起老是谈音乐,他就领着我买东西什么的。有一天在香港我真的是乱跑了,卞家白天通知我晚上有外国客人来,我堂姐也叮嘱我,要按时回来。意思是有客来,到时开饭是不能等的。我说我找同学玩去,不回来吃了。其实没这回事,我一个人逛去了。结果一逛逛到皇后大道,其实就是红灯区,有点乱,娱乐场所,我不懂红灯区这些,也不知道害怕,以为反正母亲给了我手表,到时候就往回走呗,又不是不认得路。 结果逛到很迟才回来,客人早散了,我也没想到打电话回来说一声。卞家的人很着急,听我说去了那里,板着脸说我:怎么去那样的地方?!出了事怎么向你家里交代?!我心里不服:我身上又没带什么钱,打我什么主意?其实他们是说我一个女孩子没人陪着到那种地方不安全。 喜欢到处乱逛,当然是因为对香港好奇,看什么都觉得新鲜,同时多少也是觉得待在家里太拘束。卞家规矩大—洋派,加上殖民地的味道。他们家厨子都是外国人,吃过饭端着托盘到你跟前:“Coffee or tea?”。毕恭毕敬的。吃饭时静悄悄,没人说话。我是喜欢吃西餐的,可人紧绷着,实在是受罪。有次吃完了,在客厅里,堂姐说,你弹点什么听听吧,我手足无措,问弹什么呢?她说什么都行,我就弹了《蓝色多瑙河》。堂姐本意大概是想破破没话可说的尴尬,也是洋派的社交的一套吧,我反觉得像做戏似的。当然也因为原来对有钱的人就没好感。在天津时不知是在我们家还是别的什么地方,卞家少爷少奶奶在场,议论到日本人占了天津,情况不知会怎么恶化,那位少爷就表示没什么可怕的:“We are American!”。意思是日本人不敢动美国人的。我当时听了很反感,心想,你不做中国人了?!卞白眉说可以留在香港之类,我也是格格不入的:要抗日,还怕艰苦吗? 要来客人的那天晚上我就是借故躲出去的。其实不说话也没什么,只是我就是觉得别扭。同样是洋派,在颜家我自在得多,完全没这感觉。 那段时间卞白眉留学美国的女儿正好回到香港度假,老和她爸爸吵架。为了念研究生读什么专业,她爸爸想让她念的她不感兴趣。她有大哥二哥,念书都不怎么样,她的成绩很好,卞白眉总是想让她继承他吧。他们父女俩说英文,吵架时我就在旁边,挺窘的,就低了头喝咖啡。我在天津看电影,有中文字幕,听惯了英文原声,听他们一句一句的,简直就像电影里的对话,很久以后还记得。后来在重庆中央大学,陈嘉先生让我们练习用英文写小说,我就写了一篇,题目叫什么已经忘了,只记得是写一个女孩要离开家,要革命要自由。里面写的是我自己,开头女孩与家长争执,小说第一句就是:“You demand too much of me, I refuse.”。其实就是卞家父女吵架时的原话。写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她自杀了,她有抑郁症,是在美国上吊死的。 |
热门关键词: